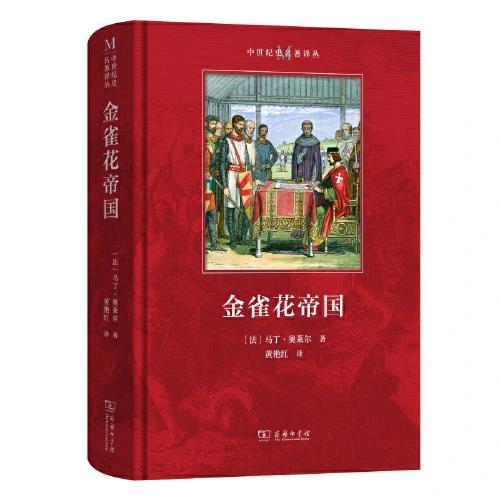
1066年,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占领英格兰,组建了一个横跨英吉利海峡的政治实体。大约一个世纪后,这个实体演变成一个中世纪西欧罕见的“安茹帝国”或“金雀花帝国”:从爱尔兰到今日法国中央高原,从苏格兰边境到比利牛斯山。但到13世纪初,随着从诺曼底到普瓦图的大片领地的丧失,这个帝国就解体了。帝国存在时间虽然只有约七十年,但它正值西欧中世纪盛期,一个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堪称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时期:从恢弘的军事和宗教建筑——如英格兰的多佛城堡和法国北方的哥特大教堂,到大学的孕育和新的骑士文学的繁荣。就各君主国而言,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鲍德温曾说,从菲利普·奥古斯都(又称腓力二世或菲利普二世)自第三次十字军返回,到他占领诺曼底前后,是卡佩王朝“决定性的十年”,而在英格兰,十来年后也迎来了其中世纪史上的重要篇章:1215年的《大宪章》。
在近代的民族-国家史学传统中,这个中世纪帝国并不受待见。英格兰注定要发展成为一个海洋帝国,因而亨利二世和他的儿子们在大陆的冒险就偏离了这条历史正道;法兰西则注定要完成“自然疆界”内的国家统一,诺曼底和安茹的大诸侯(同时也是英格兰国王)与国王的对抗就是阻碍集权和统一的“封建混乱”的典型。所以今天要重新认识这个中世纪政治实体,必须以理解并阐释传统史学在这一课题上的既有看法为前提。2004年,马丁·奥莱尔(Martin Aurell)的著作《金雀花帝国(1154—1224年)》在重新审视这个中世纪“政治怪物”时,正是从梳理学术史出发的。
马丁·奥莱尔1958年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后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著名中世纪史家乔治·杜比(Georges Duby)。他曾在法国索邦大学、鲁昂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校工作,1994年到普瓦提埃大学任教,后担任该校中世纪文明高等研究中心(CESCM)主任和《中世纪文明杂志》(Cahiers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主编。他的这种身份和经历,也许使他在类似课题上比较容易超越英国或法国的单一视角。近些年来,法国学界也开始关注跨国史、帝国史。2019年,中世纪史学者希尔万·古根海姆主编了一部《中世纪帝国》,对包括8—15世纪的中国和12世纪中叶到13世纪初的金雀花帝国在内的诸多中古“帝国”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奥莱尔的《金雀花帝国》问世时,新的学术思潮还没有形成气候。奥莱尔甚至要为著作标题中“帝国”一词的合理性做一番辩护,他随后的很多论述,也可以视为他尝试定义和描述这一中世纪帝国的基本特征。
奥莱尔最初研究的重点是封建盛期贵族的婚姻和家庭,侧重于法国南方和加泰罗尼亚等地区,这个背景无疑有利于他解读金雀花帝国的形成、发展,特别是其解体的社会史和政治史条件。金雀花帝国的形成主要源自两次婚姻:第一次是1128年安茹伯爵美男子若弗瓦(Geoffroi le Bel)与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Matilda)的婚姻,正是这位若弗瓦获得了“金雀花”(Plantagenêt)的外号,而玛蒂尔达则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的寡妻。第二次是1152年若弗瓦的儿子亨利与阿基坦的埃莉诺(Aliénor d’Aquitaine)的婚姻,前者当时已是安茹伯爵兼诺曼底公爵,后者的前夫是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二婚时是阿基坦的女公爵。1154年亨利成为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后,他就将征服者威廉奠定的英格兰-诺曼底政治体扩大到了安茹和阿基坦等地,并通过征战和联姻,使其影响力远及爱尔兰和布列塔尼等地,从而在欧亚大陆的最西端建立起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但缔造这个帝国的两次婚姻,甚至在亨利二世的廷臣中间也受到诋毁。奥莱尔对此类负面看法产生的原因做了一些分析。对帝国家族的婚姻和家庭关系的批评主要来自教士出身的文人,他们的斥责自然带有规范世俗贵族婚姻的道德动机,但另外两个因素也很重要。一方面,这些文人深度卷入帝国宫廷的名利角逐,他们遭遇挫败之后的怨恨需要有个出口;另一方面,亨利二世家族内部父子、夫妻、兄弟之间连绵不绝的争斗引发持续的政治动荡,家庭婚姻方面的失德就成为这些教会道学家的方便解释。
宫廷文人揭示的问题,需要以新的角度进行阐释。奥莱尔有个大胆的说法,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所谓“风俗的文明化”,无须等到17世纪的凡尔赛宫廷,在亨利二世的宫廷中就已经开始了:这里不仅是分配名利和恩宠的中心,而且是规训骑士行为的发源地,1175年前后,亨利二世的礼拜堂神甫埃蒂安·德·富热尔(Etienne de Fougères)就写了一部《风度手册》(Livre des Manières),以训示粗野贵族如何显得举止体面。不过,与路易十四的宫廷相比,亨利二世的宫廷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一点与其帝国的中世纪特性颇为契合。其宫廷处在不断的迁徙之中,国王需要经常亲自现身以彰显王权的存在,甚至需要亲自处理地方纷争。“因巡视而占有”(Besitzergreifung durch Umschreiten),亨利二世的做法与封建时代卡佩君主们并无二致。另外,其宫廷内部的关系,并不像凡尔赛宫廷那样等级森严,国王也远不是神一般的人物。亨利二世看上去平易近人,经常当众喜怒于形。这些现象不禁使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中世纪国王权威,即使在亨利二世这样的强势君主那里也远没有走向路易十四式的“抽象化”。
奥莱尔认为,宫廷出行路线的空间分布,很好地反映了金雀花帝国的政治结构和治理模式。通过对亨利二世的旅行轨迹和在各地逗留时间的分析,可以发现他在诺曼底和英格兰逗留的时间特别长,但其父系故地安茹,他却去得不是很频繁,至于妻子的领地阿基坦就去得更少了。国王在诺曼底和英格兰拥有最致密的治理系统,这里提供了帝国的主要经济资源,所以他对这个核心地带最为关切;相比之下,国王对安茹的控制不够有效,阿基坦、布列塔尼等边缘地带的自治性就更强了,所以国王对这些地区的关注就相对少了。这一中心-边缘的结构——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等军事边疆——看来与历史上的很多帝国并无差别。
这种政治空间格局,既有利于将骑士的战争能量引向边缘和边境地带,也可以在这些地区安顿帝国家族不安分的成员们。但家族内部争斗不断的历史表明,这个策略看来并不奏效。亨利二世的宫廷常年在外奔波,这使得国王夫妇对子女们缺少关爱,当儿子们渐次成年、纷纷要求分享权力,而父亲的吝啬和戒备心经常令他们失望时,亲情的疏远随之激化了利益纠葛。奥莱尔特别强调,1173年的大叛乱就是帝国内部各种紧张关系——首先是亨利二世与儿子们的紧张关系的一次大爆发。当时道学家们对金雀花家族的乱伦指控、安茹家族的母系起源是位不祥的女精灵的传说,既是时人解释乱局根源的一种方式, 甚至也成为家族成员的某种自我诅咒:狮心理查在听到自己的家族传说之后说,“我们既然出自魔鬼,最后也归于魔鬼”;他在希农城堡见到父亲尸体时的场景,似乎是这一连串家族争斗故事的高潮。
但奥莱尔提醒我们,亨利二世的家族矛盾在当时的西欧不是特例,只是与他的对手卡佩家族比起来,金雀花的内部撕裂才显得格外醒目,并且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两个王室相互竞争的结局。卡佩家族的路易七世和菲利普二世很好地利用了对手的家族矛盾,这是卡佩王朝一个世纪以来应付诺曼-英格兰强邻的策略。但在金雀花帝国时期,两个王朝之间的争斗在法学、文化象征等领域全面展开——当然还有军事对抗。
奥莱尔在书中多次提到当时西欧君主和诸侯之间的“效忠臣从”(fidélitéet hommage),对于这种典型的封建仪式的意义,他并没有做系统全面的论述。但从他的叙述来看,不能把效忠臣从作为一种构建政治秩序的规范,也不能认为各相关方面对同一次仪式有着同样的理解。狮心理查和无地约翰都曾为摆脱困境而向别的君主行臣从礼(hommage)。所以这种关系的缔结经常只是某一方或双方的权宜之计。当然,就金雀花帝国的命运而言,亨利二世及其父亲和儿子们对法兰西国王的效忠臣从关系意义重大,它成为卡佩君主,尤其是菲利普二世手中的一件重要的法律和意识形态武器。这件武器之所以有效,看来是好几种因素在起作用。首先,在与国王的关系问题上,与诺曼底公爵的暧昧不同,金雀花家族的父系源头,即历代安茹伯爵并不隐晦作为国王附庸的臣从地位,这个诸侯国的家族传说认为,安茹伯爵是国王的掌旗官;其次,如果英格兰国王、诺曼底等地的诸侯们要求其臣属对他们效忠,他们似乎也就有责任忠实于自己对于法兰西国王的臣从效忠誓言;再次,圣丹尼的苏热院长(AbbéSuger)构建的封建金字塔理论,看来使得11世纪封建堡主时代的政治紊乱有了某种秩序感,这种秩序感固然有利于卡佩,但也并非不利于金雀花家族;最后,可能更为重要的是,菲利普二世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针对一个特定的对手运用这件武器的:在无敌约翰内外交困时要求他奉还在大陆的“采邑”。无地约翰与其前任狮心理查简直是两个极端。理查看来是典型的带有“克里斯马”的领袖,勇武过人,待人慷慨,还是所谓“有文化的骑士”(milites litterati)的一员——这正是奥莱尔后期一部著作的标题——但他的这个弟弟无地约翰性格缺陷很大,在骑士和廷臣中毫无号召力,当战事不利时, 封君要没收他的采邑、地方贵族想解除对他的忠诚,封建法就有了实在的用途。
作为金雀花帝国的核心地区之一,诺曼底如此迅速地归附卡佩王室,无疑揭示了金雀花帝国作为一个人为政治构造的脆弱性,这个事实本身或许表明,在封建盛期,地方性政治身份与现代民族认同迥然不同。但这并不是说,金雀花的君主-诸侯们没有构建更具独立性的政治体、扩大其政治影响力的意识和行动,尽管他们的做法并不总是具有条理性和一致性,就像他们在臣从效忠方面的矛盾处境一样。奥莱尔较为详细地描绘了金雀花家族的国王及诸侯们的戴冠礼(couronnement)和加冕礼(sacre),尝试解读其中的政治意蕴;学界对王权的此类仪式素有关注,但在奥莱尔的笔下,诸侯的就职仪式也是颇具解读空间的课题,如阿基坦公爵的就职仪式是在好几个地方、分好几个阶段进行的。金雀花家族意识形态建设的另一个领域是在文学和史学等领域,它已经意识到文字的宣传功能。奥莱尔近年来对中古盛期的文化史用力颇多,如关注亚瑟传奇的意识形态功用,而《金雀花帝国》一书已经展现了他对此类课题的兴趣。如果说卡佩逐渐将查理曼视为自己的祖先,并广泛利用“加洛林题材”作为宣传工具,金雀花的廷臣文人们则在“布列塔尼题材”中发现了亚瑟王,并尝试把这个传说中的骑士改造成王朝的祖先。在亨利二世宫廷的直接或间接推动下,有关亚瑟王及其麾下骑士的武功歌和传奇纷纷出笼,这些作品带有显明或隐含的宣传动机。此外还围绕亚瑟王“发明”了一些传统,如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亚瑟与桂妮芙之墓。金雀花的吹鼓手们还利用“帝国与学术转移”(Translatio Imperii et Studii)这一母题为自己的王朝服务:既然这个主宰世界历史的转移是自东向西的,位于已知世界最西端的金雀花帝国就是这个过程的逻辑终点了。
不过与卡佩家族比起来,金雀花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竞争方面还是存在一些劣势。卡佩与教会的关系比金雀花君主和诸侯们更为融洽,与路易七世的虔诚比起来,金雀花推崇的是一种带有浓厚骑士色彩的文化,这不禁让人想起乔治·杜比在《三个等级》中的一个论点:正是在金雀花治下的法国西部,12世纪后期的作者尝试把骑士提升到比教士更高的阶层,这是对11世纪初法国北方主教们的三等级想象的重大改造,因为在后者,教士是居于首位的。但过分张扬骑士做派无疑让亲教会的文人感到不快。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卡佩的领地虽然狭小,但它是当时西欧的文化教育中心,很多为金雀花宫廷服务的文人,都是在卡佩领地内的学校接受教育的。卡佩的这个优势,在1170年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t)遇刺后亨利二世的困境中可以显示出来。不过若要全面评估这些因素的影响,仍需更为精细、范围更大的研究,奥莱尔在这里只是提出了一个有潜力的课题。但他偶尔提及的方法论,倒是能给我们某种启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法,是他在考察宫廷人文时提倡的集体性人物志(prosopographie)方法,即通过对众多历史人物的社会轮廓的准确信息的综合分析,得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结论。由于近来数字人文的发展,此类研究看来可以深入展开了。
就研究方法而言,奥莱尔《金雀花帝国》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应该还有他的历史人类学视角。在法国中世纪史学界,历史人类学方法已被以勒高夫及其弟子让-克劳德·施密特(Jean-Claude Schmitt)为代表的学者运用到诸多课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在奥莱尔处理亨利二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冲突,以及分析这位大主教遇刺时细致的场景还原中看到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在前一个问题上,奥莱尔分析了“吻”这一仪式性动作在诱发和激化两位主角之间矛盾中扮演的角色。不过从他的分析来看,国王和大主教对亲吻礼的理解并不一致,这是引发双方冲突的重要原因。像前文提到的臣从效忠礼一样,看来“和平之吻”(osculum pacis)也不能被视为规范性和秩序化的仪式,贵族武士和高级教士之间很可能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但在详细描述亨利二世的四个武士杀害托马斯·贝克特时,凶手动作的政治和社会意涵看来是清晰可辨的,这些了解国王与大主教矛盾根源的刺客,显然知道他们行动的意义所在。奥莱尔的场景还原和意义辨析揭示了这场冲突的性质所在。
以上只是译者对这部著作挂一漏万式的介绍和一些粗浅的理解,作者在书中所展示的宏大而丰富的历史场景,非有全面深入的阅读不能领会。当然,由于作者述及的问题很多,该著亦有尚可完善之处,如一些同时在大陆和不列颠诸岛拥有家族产业的贵族世家,在金雀花帝国和卡佩王朝的最后冲突中采取何种立场,作者的着墨太少。
最后可以根据奥莱尔的一个看法,就金雀花帝国这一话题的当下意义做一点延伸。他认为,尽管这个帝国在13世纪初就已解体,但在百年战争中,另一个横跨海峡、在地域上与这个帝国颇为接近的政治联合体再次浮现,这次主要依靠的是武力。这个事实表明,19世纪民族-国家史学传统所鄙视的这种跨国怪物,并不是那么绝对的历史反常现象——相应地,民族国家的孕育和形成,也并非那么绝对的“历史必然”。
对于近年来英国与欧洲关系的变化,金雀花帝国或可提供另类的视角。最近离世的著名历史学家约翰·波考克(J. G. A. Pocock, 1924—2023年)曾提出过“新不列颠史”,强调近代英国的大西洋特性,致力于对不列颠身份的“去欧洲化”。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历史话语可以为英国脱欧背书。他的这些论点当然可以找到很多历史证据。但奥莱尔的论著则提供了反向的论据。如果考虑到波尔多、拉罗歇尔和加莱这些大陆海港城市与英国延续很久的特殊联系,波考克论说的片面性似乎就更明显了:既然英国已经丧失海外殖民地,回归与大陆的传统关联就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历史的丰富性看来可以为各种非常不同的政治抉择提供论据。对于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首先应了解并理解这种丰富性。期待奥莱尔的这部著作能在这方面有所促进。
译者想就一些专有名词,特别是人名的译法做一点说明。法语和英语在此类名词的拼写上经常有不小的差别,法文中的Giraud de Barri,英文中一般写作Gerald of Wales,即威尔士的杰拉德。而且这个人名还有其他的写法。除较为知名的人物之外,本书在翻译时一般遵照法语拼写,并附注原文,读者可以自行查找英文拼写。这样做也是为了提供一个展示文化多样性的契机。另外,由于书中运用了一些富含历史和政治文化意蕴的术语,如12世纪史家笔下的“布列塔尼人”或“布立吞人”等拼写相近或一致的名词,很可能只有考虑作者的具体语境才可确定其译法。但在这方面,译者自觉相关处理未尽人意,期待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翻译得到奥莱尔教授本人的支持。商务印书馆郭可女士对译稿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杜廷广先生为文稿编辑工作付出了很多努力。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金雀花帝国》译者序(节选)
转自“碎金书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