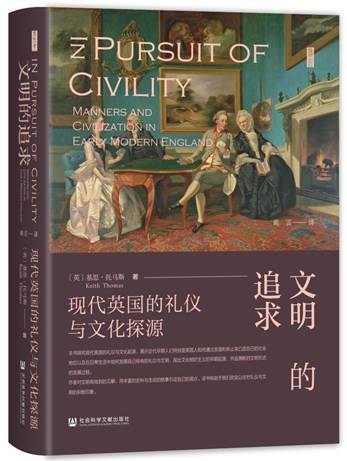
[英]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著
戴雷 译
出版时间:2025年1月
ISBN:978-7-5228-2660-8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探究现代英国的礼仪与文化起源,向我们展示近代早期人们特别是英国人如何通过言语和举止来凸显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发展自己特有的礼仪与文明,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早期起源,并追溯新的文明形式的发展过程。作者对文明有独到的见解,用丰富的史料与生动的轶事引证自己的观点。该书有助于我们改变以往对礼仪与文明的刻板印象。
作者简介:
[英]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为《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和《人类与自然世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荣誉院士。曾任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副校长、《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顾问。1988年因对早期现代英国历史研究的贡献,被女王授予骑士爵位。在知名历史刊物《今日历史》创刊六十周年的历史学家评选上,基思·托马斯是仅有的被三位专家推选的史学大家。
译者简介:
戴雷,英国德蒙福特大学翻译学博士,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现为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化与翻译。
基思·托马斯的著作《文明的追求》阐释了近代早期文明思想和文明化进程在英国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思潮,展现了基思·托马斯丰富的创新见解、对史料的把握能力,同时指出礼仪在现代世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绪论
在17世纪后期的英格兰,人们常会不经意地提及他们心中的“文明世界”、“人类中文明的那部分”、“文明的国家”或“开化的世界”。然而,他们并不总会明确指出它们是哪些文明国家。1690年,哲学家约翰·洛克问道:“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有多少?具体是哪些国家?”他自己没有给出答案,但他不认可“最文明的”国家必然是基督教国家的观点,并举例说明,中华民族就是“一个非常文明和伟大的民族”。查理二世执政时期的一位主教认为,“文明世界”包括巴比伦、阿勒颇和日本。
到了18世纪后期,东方学专家威廉·马斯登成功地将人类划分为一个由5个阶级组成的等级体系,这些阶级或多或少是“文明的”。“欧洲的礼貌、优雅的民族”排在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中国人,排在最后的是加勒比人、拉普兰人和霍屯督人。与之相反,与马斯登同时代的埃德蒙·伯克指出:“野蛮没有固定形态和级别,同样,文明优雅的单一模式也不存在。欧洲与中国的文明形态截然不同……”在随后很长的时间里,学术界都存在类似的概念划分。正如E. B.泰勒在1871年指出的:“欧洲和北美洲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实际上确立了一个标准,即简单地把自己的国家放在社会阶层的一端,把野蛮部落放在另一端,并且根据其他民族更倾向于野蛮还是文明的生活方式,相应地把它们排在这两端之间。”这是与约翰·洛克同时代的人都会认同的世界观。在他们看来,“开化之人”是那些“文明、优雅”与时尚的人,而“未开化之人”则“缺乏管教”、“野蛮”,甚至“凶残”。
......
16世纪,大多数欧洲人仍然认为区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至关重要。然而,尽管旅行家和原始民族志研究者在美洲和亚洲新发现了许多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但还是多用野蛮和文明这类非宗教术语来描述当地居民。面对丰富多样的美洲原住民文化,西班牙作家巴托洛姆·德拉斯·卡萨斯和何塞·德·阿科斯塔创造了一种围绕“野蛮”的类型学,用以构建欧洲以外民族的文明等级分类。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位于这个分类顶层的人是统治者,建立城市,制定法律,并使用文字。而位于底层的人主要是所谓的“野蛮”民族,这些民族没有任何形式的民间组织,也缺乏与其他民族交流的手段。几个世纪以来,确定野蛮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使用的术语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学者、旅行家和有其他大陆生活经验的人,并不把野蛮视为绝对情况,而只把它视作一个程度问题。他们认为文化的等级制度是渐进的,而不存在“文明”和“野蛮”之间单一、二元的区别。但对许多人来说,文明和野蛮基本的两极性依然存在,人们使用这两个词也较为随意,不会去参考民族志研究者和哲学家提供的更精细的划分标准。

在17世纪的英国,“文明人”(civil people)逐渐被称为“文明开化之人”。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术语,因为它既意味着一种条件,即变得文明的条件,也意味着一种过程,即通过摆脱野蛮而进入文明状态的过程。“开化”就是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这可能发生在一个民族身上,就像最初的不列颠人(the Britons,不列颠的原住民)一样,据说他们被古罗马人开化。这也可能发生在野生植物身上,这些植物经过培育和改良,被17世纪的园丁称为“栽培作物”。17世纪后期,文明教化的过程开始被称为“文明”(用的是civilization一词)。例如,1698年,一位作家在说“欧洲人第一次开始全面关注古希腊的文学和文明”时,就用了这个词。1706年,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后来成为院长的安德鲁·斯内普将人类聚集到“社会和政治团体”中描述为“人类文明”。法学家还用“文明”一词来表示将刑事案件转为民事案件的过程。起初,“文明”(civilization)一词用于描述文明化进程或行动,后来也用来表示文明化进程的最终产物,即文明的状态(此时与civility一词的用法相同)。人们很难说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时候获得这种新意义的。文明的最初意思渐渐地变成了另一个意思。例如,在18世纪40年代的布道中,肯特郡贝克斯利的教区牧师亨利·皮尔斯在谈到“文明、礼貌行为、外在礼仪和得体文明”时,几乎将文明视为一种条件而非一种过程。但是,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作家才明确地将那些被教化之人的状态描述为“文明”状态。直到1772年,塞缪尔·约翰逊还拒绝将这个新词(civilization)编入他的《词典》。为了指代文明的状态,即“从野蛮中解放出来”,他坚持使用“文明”(civility)这个更古老的术语。
它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个意思令人捉摸不透且不稳定的词。然而在近代早期,尽管人们用它来表达各种意义,但所有意义都以某种方式与一个有公序良俗的政治共同体相关,也与公民应有的得体素质和行为有关。16世纪早期,英语中的civility一词,就如同它的意大利语和法语前身一样(分别是civiltà和civilité),更广义地指代非野蛮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人们后来了解的civilization。“文明”(civility)意味着一种静态,人们并没有将文明化视作一种过程。16世纪,civility一词还用来表示礼仪、礼节和礼貌行为的狭义概念。正如“用普通礼貌待人”中的“礼貌”一词用的就是civility。正是因为civility和civilization这两个词在意思上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詹姆斯·博斯韦尔才力劝约翰逊将其《词典》中civility的定义限定为“礼貌”(politeness)或“言行得体”(decency),然后用新术语civilization来表示文明化进程,但他的劝说没有成功。
尽管约翰逊在这方面固执己见,但是civility一词在18世纪后期重新回归它的狭义:良好的礼仪和公民素质。而civilization则成为英语中一个通用的词,既可以指文明化进程,也可以用来描述开化之人在文化、道德和物质等各方面的状态。这个词被广泛使用,带着无可置疑的种族优越感,暗示“文明”国家是人类社会最完美的典范。与之相比,其他生活方式或多或少都是低劣的,是贫穷、无知、管理不善或完全丧失社会功能的产物。之后,这一臆断对塑造西欧国家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在近代早期的英国,“文明”和“野蛮”之间亘古通今的对立经常被引用,来表达当时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当时关于文明理想的论述,是在花言巧语的自我描述中进行的。当探险家和殖民者痛批他们在欧洲以外世界所遭遇的“野蛮、残忍”对待时,含蓄地表达了对欧洲生活方式的向往,通过阐述自己不是怎样的人来定义自己。与英国宗教改革后的其他令人谈之色变的事物一样,“教皇”、“巫术”和“野蛮”的概念体现了许多同时代人所深恶痛绝的东西,同时隐约揭示了他们所向往的东西。正如神学家探究罪孽的意义以揭示什么是真善美一样,“文明人”也需要有“野蛮人”这么一个概念,最好是这样的一群人实际存在,来展现他们自身的卓尔不群。文明概念本质上是相对的:它需要一个与之对立的概念,才方便人们理解。20世纪30年代,哲学家兼历史学家R. G.科林伍德写道:“我们创造了一个野蛮人的神话形象,它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历史人物,而是我们所厌恶和恐惧的一切事物的寓言象征,集我们所唾弃的邪恶欲望和所鄙视的丑陋思想于一身。”或以如今的学术用语来说,“身份是由创造出的对立形象构建的”。问近代早期的英国人,什么是“文明”,以及什么是“野蛮”,就是要探究他们对社会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基本臆断。这为我们重新思考这个主题提供了一种视角。
本书试图证明,从16世纪初的英国宗教改革到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期间,文明和文明化进程思想在英国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书揭示了这两种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思潮,描述了它们的用途,并探讨了它们受到挑战甚至遭到拒绝的一些情况。
......
第一章和第二章着重探讨近代早期的礼仪概念,包括审视礼仪在统治阶层精英确立其自身地位中所起的作用、礼仪概念对社会其他阶层的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固化了主流的社会结构。第三章探究了同处于近代早期的人们对“文明”认识的变化。第四章围绕英国如何成为文明国家,比较了人们的不同看法。第五章考察了英国人对其优越文明的信仰,是如何影响他们与“不文明”民族的关系,尤其在国际贸易、殖民征服和奴隶制合法化的视角下。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我阐释了有关近代早期文明和文明化进程的观念远远没有被普遍接受,反而受到了当代批评家的持续批判。最后,我思考了时至今日,这些文明理想的重要性,并试问如果没有它们,社会能否团结,人类能否幸福。
(节选自本书绪论,内容有删减)
转载自:社科文献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