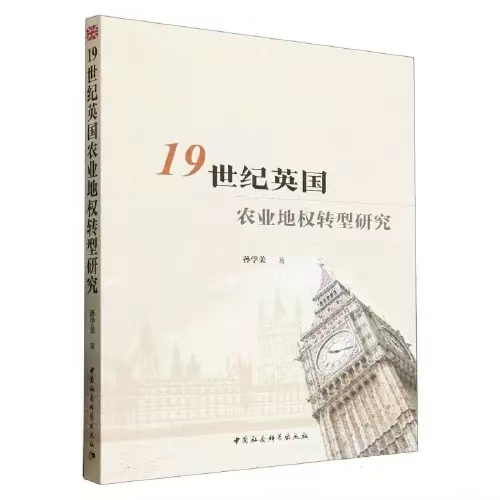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孙学美,1985年生,山东省费县人,2015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史、世界史的学习与研究工作。现任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聊城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太平洋岛国研究》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太平洋岛国史。主持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1项,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内容简介
英国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发源地,私人农地产权作为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其确权历程开启得较早,但整个过程却漫长而曲折,直至19世纪,英国农业地权仍存在诸多不明晰之处,阻碍了英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持续化发展,成为当时英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治理问题之一。该时期,英国政府发挥强大的国家宏观调控治理能力,以法律手段助推农地产权明晰化,以1894年遗产税调控农地所有权分配。经此改革,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割型农业地权不断向两权权能合一型农业地权转变,英国农业经营模式也随之由租佃农场向自有自营型家庭农场转型,英国现代农业地权和农业经营模式最终得以确立。
序言
英国是农业资本主义(Agrarian Capitalism)的发源地,私人土地产权的确立是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英国的近代私人土地产权确权进程虽然开启得较早,但其确权的整个历史进程却是漫长而复杂的,直至19世纪,土地产权仍存在诸多不明晰之处。
19世纪的英国,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土地贵族大地产盛行。对于这一时期社会形态的描述,国外一些著名学者,如罗森海姆(JamesM.Rosenheim)、明格(Gordon Edmund Mingay)、汤普森(Francis Michael Longstreth Thompson)、斯普森(David Spring)、比尔德(Madeleine Beard)等,倾向将其称为“Landed society”,国内学界一般将该词译作“土地社会”或“大土地所有者社会”。按照相关学者们的研究,英国土地社会肇始于17世纪中叶,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最终走向解体,历时四个多世纪,其影响之深远,毋庸置疑。土地社会时期,英国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地产热”持续升温且历久不衰,持有“地产”规模与价值大小近乎衡量个人经济、政治与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至19世纪后半叶,地产热弊端已致英国农业经济持续化、政治民主化发展遭遇瓶颈,成为当时英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治理问题之一。
19世纪,英国政府不断发挥强大的国家宏观调控治理能力,在以法律手段推进农业地权界定清晰化基础上,又于1894年出台了“遗产税”(estate duty),以税收调控土地所有权分配,推进农业地权变革进程,保障英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平稳转型。在政府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导向下,“僵而不化”的“土地社会”逐渐走向解体。在这一过程中,以英国农业地权明晰化为基础,土地所有权由地产主向租地农场主转移,农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两相分离的农业地权类型随之发生变化,不向所有权和经营权相统一的农业地权类型转变,权能合一型农业地权得以确立。随后,建立在权能合一型农业地权基础之上的新型农场成为英国现代主流农业经营模式。
以19世纪英国农业地权转型为切入点,系统梳理该时期英国农业地权结构由所有权、经营权两相分离的“分割型”地权向两相统一的“合一型”地权转型的相关史实及其历史变迁脉络,并就其中蕴含的英国政府以法律、税收等手段治理该时期“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地产热经久不衰”等重大社会问题的基本理念、路径和方法进行归纳分析,有助于增进学界有关19世纪英国农业发展、农业地权治理等方面的知识,亦可为农业发展、农业治理等方面相似问题的解决提供经验和历史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坚持唯物史观,采用经济社会史研究范式,基于该时期英国农业地权形成、发展、演变乃至最终走向解体的整体历史变迁实际,阐明英国政府以税收、法律手段治理农业地权不明晰问题的理念与路径。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通过细致梳理相关时段内的议会汉萨文件、法律文本、土地家族地产档案、时政报刊、地产交易数据等史料,明确大地产的形成、经营管理状况、大地产地权结构特征等史实,系统分析英国通过立法手段推进终身地权、租佃权明晰化,增进农业工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结,以及通过1894年遗产税推进大地产地权向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型地权转型的相关理念与路径等。同时借鉴年鉴学派长时段研究方法,将长时段内的英国地权与土地继承、基于土地继承征税实践以及遗嘱传统等有机结合起来,分析英国得以通过1894年遗产税治理19世纪英国农业地权不明晰问题的古代地权、地税及民众心态等深层历史原因。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选取典型土地家族大地产案例,结合相关政府、机构统计数据,借助广泛存在的同时代文献资料,客观复原该时期英国农业地权发展演变史,实证分析英国国家治理与农业地权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与此同时,综合运用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研究方法,从英国的经济、财政、法律、赋税、民众心态、社会形态等视角,多维度绘制该时期各农业地权主体包括地产主、租地农场主、农业工人在内的集体心理,真实再现19世纪英国以农业地权变迁为具象的土地社会变迁全景图。
本书除绪言、结语部分外,共包括九章。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依照19世纪英国农业地权形成、发展、演变、衰落的线性历史发展脉络逻辑主线顺次展开,将英国以议会立法方式推进终身地权明晰化、租佃权明晰化、应对农业工人起义和社会贫困问题,以及以遗产税推进土地所有权变革的税收治理措施适时融入其中,层层递进,客观再现19世纪英国农业地权变迁史实,明确其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
第一章历史基础:古代地权与土地继承税。借助年鉴学派长时段研究范式,在广泛借鉴学界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就19世纪以前的英国地权演变及基于地产继承征税实践状况做一整体考察,以明晰19世纪典型农业地权得以形成的深层古代地权与土地继承税历史背景。
第二章大地产的构建。借助大量土地家族案例,将土地家族大地产的形成原因、形成过程以及大地产租佃制运营方式与特点直观形象地呈现出来,以明晰农业大地产地权的构建路径及原因。19世纪典型农业地权机制的形成建立于近代小农土地所有权明晰化基础之上,土地家族大地产的构建与小土地所有权的消失是同一历史发展进程不同层面的呈现。租佃制是大地产的基本土地组织模式,依托该模式,主佃双方基于租佃契约,将各自资本以不同形式投资于土地之上,进而生成对双方所签订契约租佃地的不同地权要求,农业大地产独特地权结构由此形成。
第三章19世纪农业地权结构及其存在问题。着重考察该地权结构下的地产主、租地农场主的地权状况,分析其核心特征及存在问题。农业大地产上相对应的土地产权不清晰,各土地权利主体地权行使边界无明确界定,主佃双方关系主要依赖不对等传统租约、地方惯例或习俗进行调节,缺乏统一而完善的法律保证机制以维护各地权主体权利。这一权责不明晰的农业地权构成英国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需要对之做出必要的变革。
第四章终身地权明晰化。以史为证、客观分析地产主的终身地权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明晰化的。终身地权明晰化主要经由两条途径实现:一是终身地产出租权、抵押权、出售权的立法确认,二是限制终身地产自由处分权的严格家族定序授予地产制度(Strict Family Settlement)的破除。
第五章租佃权明晰化。以史为证、客观分析租地农场主的租佃权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明晰化的。租佃权明晰化是基于维护主佃双方共同权益,通过明确租佃权边界方式实现的。是主佃双方不断博弈过程中基于让步妥协在折中基础上达成的虽非最优但切实可行的相对有效方案。
第六章农业工人“地权”相关问题。系统梳理19世纪的农业工人起义、社会贫困问题以及英国政府的应对之策;系统分析该时期出台的有关份地与小持有地的法律文本及其具体执行状况,说明国家以立法手段应对农业工人流失,保障农业发展以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理念与路径。
第七章农业地产形势新变化。借助该时期留存下来的大量土地家族地产档案、农业调查报告、法律文本、相关人士回忆录、议会汉萨文件等原始史料,实证说明至19世纪晚期大地产经济形势已经严重下滑、濒于破产,土地财富已经与政治权力“脱钩”,土地的经济、政治、社会价值都已不再。以土地所有权集中为显性特征的“土地社会”“已僵”,且“顽固不化”,需要国家出台特定政策推进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提高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八章遗产税与农地所有权变革。采用回溯法深入分析1894年遗产税得以出台的历史渊源。借助土地家族地产档案、议会汉萨文件、时政报刊等文献资料,说明在1894年遗产税出台之后,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加上一战、二战等灾难性事件导致土地家族继承人频繁更换之时,面对高额遗产税征缴压力,土地家族大地产继承者不得不大规模出售其家族地产,而这些被抛入土地市场的大地产多被其租地农场主(tenant farmer)购买。借此,土地所有权由地产主向租地农场主之手转移,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合而为一,分割型地权向合一型地权转型,合一型地权时代开启。
第九章新式地权基础上的新型农场。结合具体史实说明该时期农业地权转型的基本走向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合一,而建立在该新式地权基础上的新型农场则成为英国主流农业经营方式。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合一型地权,以及自有自营农场的日渐兴起,并非英国历史上独有的历史事件,同时也是多数西欧国家农业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趋向。权能合一型农场经营方式,建立在稳定、明晰化的土地产权基础之上,在其上农业生产者能够实现完全的地权获得之感。但这种农业经营模式存在固有缺陷和不足,在当时的特定经济社会形势下,其良性存续与发展,还需要借助个体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合作,需要依赖农业科技的进步以及政府的扶持和帮助,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后记
与历史结缘,是自己人生规划中的一场意外。起初,历史感不强,又缺少本科阶段的专业历史训练,致使自己一路走来,颇多艰难。但这一路走来,不畏艰难,步履前行,虽艰难却也幸运。因历史,得遇良师;因历史,结交挚友。一路走来,也颇多“小确幸”。
从2009年至今,与历史专业相伴而行,已有十余年。在这不长亦不短的时间里,与历史从“相遇”到“相知”,再到“相携而行”。对历史由起初的“怵”,到如今的“爱”,是一场美丽的“邂逅”,也是一段难得的“修行”。在这一过程中,也越来越能理解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历史从“史”而出,以“鉴”而终。
“板凳当坐十年冷”,对从事历史研究的人而言,最是适用。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抽丝剥茧,形成具有一定严密逻辑的历史观点或思想,绝非易事。单是搜集、阅读、整理史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不只是时间和精力,还更得要有一颗能沉得下来的心才行。只有沉得下心来,才能冷静、客观地从杂乱、浩繁的史料中寻出一丝可为己、为国家、为社会所用的“思想”。这最后的最后,才是动用逻辑思维,借助严密的史料实证,将这一“研究结果”真实地呈现出来。
本书的写作始于2014年,至今已满“十年之期”,在这十年里,几易其稿,始有目前的样。
这部书稿,不仅仅是自己学习与研究期间所学所思的一点成果,更是我人生阅历的一点感悟。我是一名出生于农村的孩子,是自泥土里摸爬滚打着长大的。自学龄时起,虽多数时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但在上学读书之余,也常会帮父母做一些田地里力所能及的农活,即便是在进入大学之后,每逢假期,也常会回家帮母亲干一些农活。一路走来,我并没有因为读书的缘故,而在家里逃避做农活,每当我回到村里时,“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村人”。这样的人生阅历,使得人文知识和土地生活早早地水乳交融式地在我的血脉之中流淌,也渐渐地使我对农业、农民、土地产权问题产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情感和认识,而这些情感和认识,正是本书写作的最为原始的起点。与此同时,也正是这一人生经历,让我对农业、农民、土地产权相关问题的分析,受制于我生于农村,以及我长年累月地间或从事农活的实践,打上了一些不够客观和理性的印子。
这部书稿的完成,尤其要感谢我的恩师侯建新先生。这部书稿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而我的博士论文的论题选定,框架结构组织、调整,论文核心思想的把握,乃至整体内容的写作与编排,都花费了恩师侯建新先生大量的心血。离开恩师无私的帮助,便不会有这部书稿。当然,我对恩师的感激还不仅仅局限于这部书稿,它同样凝结在我过往全部的学习和日常生活之中。最初,愚笨且不自信的我,从未奢望能成为先生门下的一名弟子,承蒙先生不弃,收下了我这个愚昧而蠢钝的徒儿,并一点一点地指引着我,使我一步一步地踏入了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如果不是先生似无边大海般的容人之怀,如果不是先生因材施教型的育人方法,如果不是先生高屋建瓴式的学术点拨,如果……便不会有我的今天。师恩绵绵,没齿难忘!徒儿无以为报,唯有在历史研究领域历久钻研下去,唯有更好地担负起历史学人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唯有倾己所能为国家、为社会尽一点绵薄之力。
此外,也要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在我读博期间,没有他们在背后的强有力的支持,我很难安心地在学校里学习。当时,即便是在我儿子生病之时,母亲也很少告诉我,怕影响我,使我不能在学校里安心学习。因而,对于父母,我是万分感激的。
最后,感谢陈德正老师。陈老师信任并无条件地资助了本书部分出版经费,他总是鼓励我全身心地投入书稿的修改工作,且不辞劳苦,与编辑部其他老师一遍又一遍地仔细校对书稿,一直容忍我来来回回地修改完善书稿,直至本书最后出版,对此万分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