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了!去年这个时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向亚军、余新忠为大家做了年终盘点,其中写道:“新冠疫情爆发两年来,对人类社会及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一时间历史上的瘟疫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瘟疫对于人类社会以及文明进程演进的影响成为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由此出发,他们检讨了医疗史这一史学流派的新发展。
让人扼腕的是,一年之后的今天,疫情在全国各地,又呈现卷土重来之势,让人不得不感叹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前者虽有“万物之灵长”之美誉,其实十分渺小和无力。的确,从历史的全球走向而言,近代以来高悬之“人定胜天”的理想或许仍有其吸引力,但今天各国史学同行的态度则愈益倾向与自然界和谐共处,对人所赖以生存的居所——地球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主张抱持一种妥协宽容乃至自我反省的态度。或许,中国古哲所倡言的“天人合一”的思维特征,尚能反映和形容当代史学观念演变的大致趋向。自本世纪以来环境史、“大历史”、动物史和生态史等的蓬勃发展,便是有力的例证。这些流派虽然研究的侧重点各各不同,但都强调突破原有的时间观念,不但走出民族国家的视角,超越国族史的书写传统,而且还竭力主张超越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思维,也即“将人类去中心化”(de-centering human)。这些研究的目的是,由外而内,从动物、植被、微生物、海洋、地球乃至宇宙的角度考察人类历史的演变,指出欧洲近代史学观念的虚妄和局限,从而彻底摆脱“西方中心论”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中心论”。
今年八月,笔者有幸参加了推迟两年举行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像往年一样,这次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行的大会,安排了四个层次的讨论,包括主题发言、专题发言、圆桌会议和附属学会所组织的专场讨论。主题发言是其中的重点,共有三场,而重中之重则是第一场:“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Intertwined Pathways: Animals and Human Histories),持续了整整一天。毋庸赘言,这一场的重点是指出:在世界历史的演变长河中,人类从来就不是孤军作战,而是与动物和所有其他有机物共存共荣、相互依赖的过程。[1]而在大会的开幕式上,还有当代史学理论界十分活跃、芝加哥大学的讲座教授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发言,讨论开展“地球史”研究之必要。有必要一提的是,查克拉巴蒂发言所用的“地球史”英文原文是Planetary Histories,不但是复数,而且更有“行星史”的意思。[2]换言之,他所倡导的“地球史”,其意图是考察宇宙间地球作为其中一颗行星的历史,从一个角度着力体现“大历史”所倡导的“去人类中心”的宏观史学观念。
依笔者管见,以上的举例说明,当今史学界正在出现一个如本文标题所言——重建“宏大叙事”——的最新趋向。为了交代明白,我们或许有必要先简单讨论一下“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或“宏大叙述”这一概念。“宏大叙事”与“元叙述”(metanarrative)相同,是两个词语的组合。“宏大”(grand)一词浅显易懂,而“元”(meta)原是希腊文,包含“超越”的意思,所以有台湾地区学者(如黄进兴)曾将之译为“后设”,其实“形上”也是meta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译法,其著例便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所谓“叙事”或“叙述”(narrative)一词,与常用的“故事”(story)一词意思相同。在英文中,“历史”是history,有人将之拆解为his-story或His-story,后者隐含表示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旨意下所展开的一个“故事”。上面这些字词的讨论,或许有点繁琐,但其实有助我们理解“宏大叙事”的真切含义,那就是有关人类历史之意义、经验或知识的一种形上的、也即更高层次的理论思考。这一思考预设了一个主导思维,试图为社会的演变(包括已变的和未变的)提供某种合法性,显示了目的论的视角。举例而言,史学界许多人熟悉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便是近代以来“宏大叙事”的一个典型。黑格尔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即是走向自由,其手段是通过理性的运用和扩展。由此前提、也即“元叙述”出发,他的《历史哲学讲义》从东方开始,东方社会的特点是,唯有统治者一个人享有“自由”,其他人都只能是附庸。然而经过理性的不断延伸,从东方转移到西方,自由的程度也得以不断提高,其标志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使百姓变成了公民,后者不但享有一定的自由,而且还有与统治者共同治理国家的一定的权利。
由上例看出,“宏大叙事”可以是历史哲学的别称,也即思想家对人类历史演化的形上概括、总结。但两者之间也有重要的不同。自人类文明开始以来,便有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哲学思考,而“宏大叙事”主要指的是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的历史哲学。与之前的思考不同,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具有下列特征:(1)历史不断进步;(2)进步是一线的,也即各个民族将会沿着同一个方向演进;(3)历史演变既有起点又有终点(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就是一个显例,以原始共产主义开始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为结束)。
“宏大叙事”的提法在上世纪初已经出现,而法国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在1979年写作的《后现代情境》一书中,对其做了具体的论述。饶有趣味的是,利奥塔分析了“宏大叙事”的概念,目的并不是强调其重要和适时,而是为了对之进行批评和超越。他强调二战之后科技发展和社会变化的背景下,人类历史已经迈入了“后现代”,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家所倡导的历史哲学观念,特别是历史一线进步的观念,已经不敷需要、落伍时代了。
利奥塔检讨“宏大叙事”,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做了铺垫,启发后人重新思考历史的演化和走向,渐渐走出唯西欧马首是瞻、视其为历史发展领头羊的思维传统。对历史学中“宏大叙事”的反省,主要始自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出现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和思潮,如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反文化”(counter-culture)和性革命等,有助促使学术界对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和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到了七十年代,出现了包括利奥塔《后现代情境》在内的一些有所争议又启发新知的著作,如1972年阿尔弗瑞德·克劳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1973年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史学》、1976年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瘟疫与人》和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这些著作与六十年代福柯已经出版的《词与物》和《疯癫与文明》等一道,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和定位西方文明在近代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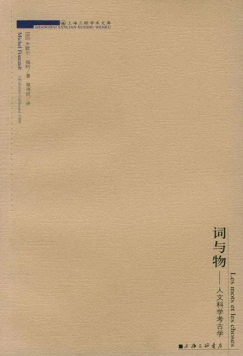
《词与物》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些著作的启发性在于帮助我们反省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之间复杂的关联性,认识到人类虽然具有并且能够运用理性,进行了科学革命并实施现代化,但远非力大无穷,能在自然界天马行空、无往不胜。克劳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一书的副题是“1492年的生物和文化的结果”。他的写作意图是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历史意义。在原先的相关著作中,哥伦布、达伽马等欧洲航海家,被塑造为孤胆英雄,以一己之力改造历史。但克劳斯比指出,欧洲殖民者之所以能“轻易”征服美洲,并不完全靠的是科技的先进。他在该书的第二章便指出,欧洲人抵达美洲的一个世纪内,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锐减,原因是他们长期生活在“世外桃源”中,对欧亚大陆流行过的瘟疫病毒,没有任何抵抗力。[3]克劳斯比在数年之后,又出版了《生物帝国主义》一书,更强调欧洲能成为近代历史的领军,在世界各地殖民和建立“新欧洲”,主要靠的是生物的而不是军事的因素。

《瘟疫与人》
麦克尼尔在《哥伦布大交换》问世四年之后出版的《瘟疫与人》,从更广博的视角,以整个人类历史为对象,描述人类如何与不时发生的瘟疫之间形成的张力和互动。他与克劳斯比一样,怀疑之前有关欧洲人“大航海时代”的“宏大叙事”:欧洲人似乎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成功地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了人数多的不成比例的美洲印第安人”,从而轻易体现“基督教的真理性”。但麦克尼尔则认为:“欧洲文明固有的魅力以及西班牙人无可否认的技术优势并不足以解释古老的印第安生活方式和信仰的全面崩溃”。他略作深究便发现,其实英勇好战的阿兹特克人在与西班牙人交手之时,便已受到了天花的袭击。从瘟疫与人类关系的视角出发,麦克尼尔还指出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200年之间,是“欧亚大陆瘟疫疾病的大交融”时代:瘟疫的流行不但阻遏了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皇帝重振罗马帝国的雄心壮志,而且还长期阻挡了中国文明在南方的扩展。他对后者的解释是,汉帝国虽然在形式上已经拥有长江以南的流域,但南方的全面、快速的开发则要在汉亡之后的几百年后才得以显现。[4]他的推测,让人想起古书中经常记载的南方丛林中的“瘴疬之气”,如何迅速吞噬贸然进入的军队。这些所谓的“瘴气”,应该包括侵袭呼吸道从而感染人类的各类病毒。

《哥伦布大交换》
上述克劳斯比和麦克尼尔的两部著作,其贡献在于转换了历史研究的视角,从注重革命、探险和征服等人力的作为,转向考察人和自然以及其他生物的张力和互动,从而有助修正原有的现代性论述,走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这些起初的尝试,颇费周折。克劳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成书之后,几经曲折,才找到了一家普通的出版社出版。但问世之后,影响深远,2003年又出版了该书三十周年纪念版,由威廉·麦克尼尔之子、环境史的专家约翰·麦克尼尔作序,为之热情推荐。同样,威廉·麦克尼尔之写作《瘟疫与人》,也经历了长期的思考。他在1963年出版了《西方的兴起》,一时声誉鹊起,但《瘟疫与人》的构思和写作,则让他准备了十余年。《西方的兴起》书名显示他的写作意图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名作《西方的没落》有关,似乎为的是与之唱对台戏。此书在冷战时期出版,大受欢迎,也许与此耸人听闻的书名有关。但其实并不尽然,因为该书的副题是“一部人类共同体的历史”。麦克尼尔在写作中借鉴了斯宾格勒、汤因比“文明形态论”的方法,将西方在16世纪之后的兴起,与之前在其他地区昌盛的其他文明相提并论。而《瘟疫与人》的写作,则以瘟疫为视角,从描述人的历史扩大为考察人与其他相关生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生物史”。

《西方的兴起》
在讨论当今学术界重建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前,笔者还想交代一本富有开拓性的著作,那就是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1997年出版的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如果说上面麦克尼尔检查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瘟疫为媒介,借助了生物学的方法,那么戴蒙德的视角更为扩大,试图构建一部如他所说的“人类史”。其实,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可以称作为一部以人为中心的“地球史”,因为他不仅考察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互动,而且还从整个地球几大板块出发,讨论了欧亚大陆的特殊性,由此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当然,如书名所示,戴蒙德也讨论了病菌与人类之间的复杂关联。农业革命之后,欧亚大陆的许多居民开始定居并蓄养家畜,而当地的优势在于:马、牛、狗、猪、羊等动物易于驯养,很快与人类建立了亲密的互动和依赖关系。它们不但为人类提供了食物,特别是动物蛋白,促进了人体和大脑的发育和生长,而且还充当了人类交通和交战的助手。与此相较,美洲大陆因为没有同样的动物,因此其历史的演化轨迹不同。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但是,戴蒙德在书中专辟一章强调,人类驯养动物、与之亲密接触虽然让欧亚大陆领先于其他地区,但同时这些牲畜也给人类带来了“致命礼物”,那就是各种细菌和病毒,导致传染病的间歇爆发,因为迄今为止所有在人类中流行的传染病,都是从与人亲密互动的动物身上传来的,如牛带给人类的有麻疹、天花和肺结核,而流感则来自猪和鸭。上面提到的西班牙人将病菌带到了美洲,导致当地人口的锐减,自然是一显例,戴蒙德在书中也详细描述。但他同时强调,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其实屡见不鲜:“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的病菌”。他用“闪电战”和“游击战”来形容病菌侵袭人类的方式,也即病毒有爆发期和之后的转移期,后者是为了找到新的宿主。而他更重要的发现是,“与世隔绝”的人群,受到的伤害最大,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病毒,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免疫能力。据戴蒙德的估算,欧洲人到了美洲之后,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从2000万降到100万,损失了95%。同样,长期处于“世外桃源”的太平洋岛屿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在接触了欧亚大陆的病毒之后,人口下降了50%-100%。[5]
克劳斯比、麦克尼尔和戴蒙德的研究,为当代学者重建历史的“宏大叙事”,做了理论上的重要准备。不过如同上述,他们的研究虽然指出了人类必须而且必然与自然界的万物共生共存的现象,但他们采用的视角,还是以人为中心的。而当代环境史、大历史和动物史的研究,则往前迈进了新的一步,尝试转换视角,站在与人相关的另一方的立场来书写历史。比如上面提到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有关动物史的主题发言,一共有四组讨论,而第一组就探讨了“动物的主体性”,也即不把人如何驯养动物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是希望从动物的视角看待它们与人类的关系。这一企图无疑有着相当的方法论难度,因为动物自身没有留下文献史料,如何描述它们对人类的态度好恶?但其实二战之后历史学的发展,已经让史家在方法论上有了重要的突破。比如借助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史家能对社会下层和边缘等“无声”的团体,做出描述和分析。同理,通过观察动物的肢体动作和语言,动物史家也能尝试如何设身处地地理解动物的心理,突显其“主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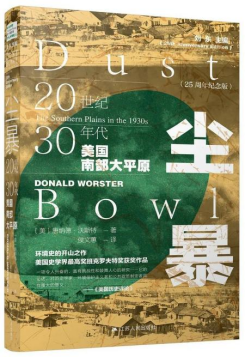
《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
当然,尝试从人的对方写史,在历史学中“将人类去中心化”,在环境史和新近流行的“大历史”中,更为普遍。美国环境史的领军人物、在堪萨斯大学退休之后曾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唐纳德·沃斯特教授的成名作《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是一个初期的尝试。此书于1980年出版之后,多次再版,被誉为美国环境史的开山之作。从其书名便可发现,沃斯特有意将“尘暴”这一自然灾害作为书的主体内容,由此来探讨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近年类似取径的环境史著作,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譬如最近译成中文的《冷杉与帝国:近代早期中国森林的转变》便是一例。此外还有《美国草原:大平原农业意料之外的俄国渊源,1870s - 1930s》、《能源帝国:煤炭如何制造中东并引发全球碳化》和《战火中的自然:美国环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都是这两年刚问世的著作。限于篇幅,笔者无法在此细谈它们的具体贡献。

《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
开展“大历史”研究的前提,便是要更改时间的内涵,指出人类在历史上微弱、渺小的位置。“大历史”的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著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其中他提出了一个量化的说法:假如将整个130亿年的宇宙演化史简化为十三年的话,那么人类的出现大约是在三天前。农业文明的初始发生在五分钟前,工业革命的发生不过六秒钟以前,而世界人口达到六十亿、二次大战和阿波罗登月都只不过是最后一秒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认可这一点,那么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的“宏大叙事”,便自然土崩瓦解了。在“大历史”的观照下,历史是否进步、历史是否有起点和终点等问题,都需要加以完全彻底的重新考量。“大历史”的研究同时也跳出了近代史学的传统视角,如国家、民族、种族、宗教等。而从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十分畅销的《人类简史》来看,这一尝试“大历史”的努力,已经从学界走向了大众。总而言之,如果说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在黑格尔的时代曾经是历史学的“宏大叙事”,那么从新近史学的最新发展来看,这一传统既不“宏大”也不重要,因为相较人类史、生物史、地球史等“大历史”,源自西欧的现代世界五百年,渺如沧海之一粟,天下间之蜉蝣。重建历史“宏大叙事”的最新努力,或许将让我们最终走出至今缠绕不去的西方中心论。
(2022年12月27日写于上海并感谢杨晶晶在资料上提供的帮助)
[1]“Program,”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2020/2022, 28-29.
[2]见Dipesh Chakrabarty,“Capitalism, Work, and the Ground for Planetary Histories,”in“Opening Ceremony,”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2020/2022.
[3] Alfred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T: Praeger, 2003, chapter 2.
[4]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缘起”和第三章。
[5]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主要见第十一章。
原文载于:澎湃新闻;转载自:学忍堂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