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Rural China 创刊十周年,特组织“中国小农经济往哪里去”主题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学者撰文讨论,并推出纪念特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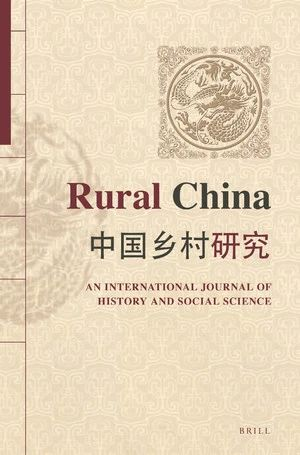
本专期关注的议题首先是小农经济在中国所展示的顽强生命力,特别显著地可见于笔者文章称作“新农业”在近几十年中的广泛兴起。其中,最重要和突出的是高附加值的“设施小农业”(特别鲜明地体现于1、3、5亩地的拱棚蔬菜和小规模的果园),2010年以来便已占到农业耕地面积的大约1/3, 农业生产总值的2/3。它们所反映的是中国人食物消费从8:1:1的粮食:蔬菜:肉食模式转入4:3:3的模式。同时,2018年以来,国家已经展示了前所未见的对小规模农业的重视,更正了多年来关于现代农业只可能并必须是围绕“规模经济效益”教条的错误认识。
这阐明的首先是,恰亚诺夫关于农业中的“差异化最优”理论:不是越大越好,而是不同的农业生产具有不同的最佳规模,尤其鲜明地展示于蔬菜种植中小规模设施农业的巨大生命力。同时,也突出了恰氏关于小农业连接大市场的“纵向一体化”理论——即其应对大市场所必须的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藏、运输、销售方面的服务和相应措施。
固然,正如陈义媛教授的文章所论证,在“大田”粮食(和棉花)农业方面,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一定程度的规模化倾向——尤其是粮食种植中的机耕播收服务的扩张。陈文特别关注规模化营利资本在这样的服务中所起的作用,并给出了具体实例和依据;同时,陈文也论析了这种资本所面临的供给过剩等困难和挑战,不是一帆风顺的扩增。
在笔者看来,我们需要清楚辨别,首先是陈文所讨论的规模化服务中的资本大多既非生产性的机械化产业资本也非生产性的新农业中的“设施资本”,而是商业资本。至于真正经典理论型的雇工经营产业资本,我们须要清楚说明,2006和2016年的两次权威性全国农业普查证实,它们仍然仅仅占到农业总劳动力中的3%,十年间并无显著的扩增。当然,2016年后的情况尚有待于2026年的第三次普查来确定。
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陈文没有考虑到的另一种重要现象——即如今不少小农户家庭的成员,由于其非农兼业的较高回报(“机会成本”),会选择购买机耕播收服务来腾出更多时间从事更高回报的非农就业。这是源自小农户兼农业与非农业生产之后的一种选择,不简单是源自资本主义扩张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不可像有的论者那样借助经典马克思主义(或经典自由主义)理论的教条——即“传统”小农经济必将会被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取代——来认识陈文所说明的实际和其前景。
本专期处理的第二大问题是欧阳静教授讨论的,原先由笔者提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概念——即中国长期以来在中央集权之下,仍然在基层治理方面展示了“简约治理”惯习,不可将其简单等同于一般意义的西方式的(低度中央集权但)高度渗透基层的科层制行政模式。实际上,乃是一种处于“第三领域”中间地带的行政与民众二元互动的状态。今天,我们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看到那样的简约治理的有限持续。虽然,正如欧阳静,根据其长期积累的关于县级及其下的治理研究,明确指出,近年来的总体趋势无疑是越来越高度的行政官僚体系化。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还可以看到与其不同的简约治理现象,特别展示于一些党政与社区合一的基层相对简约的社区治理。在笔者看来,一个突出的经验实例是结合“党建”与村庄集体运作的烟台经验(下面还要讨论)。殴阳静和笔者都认为,最适合中国基层小农经济和村庄社区的治理模式仍然是由农村社区自身来参与对接大政府和大市场,而不是简单的由上而下官僚化、行政化模式。
杨团教授的文章更直白地倡议,最理想的基层治理模式绝对不是简单的由上而下的高度中央集权和高度渗透基层的官僚主义治理模式,也不是西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而是像四川战旗村那样的模式——即结合村庄土地集体所有和嵌入村庄社区基层党支部的领导,来服务社区成员及其集体,而非简单的官僚化治理或市场化营利。也就是说,既非简单的集权由上而下官僚主义行政模式,也非简单的逐利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而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集体经营模式。
这就和我们多位学者,包括笔者在内,所突出的山东烟台地区兴起的、围绕基层“党建”带领的模式紧密相似、相关,既超越资本主义模式,也超越由上而下的行政化官僚主义模式。(于涛2019;江宇2020;陈义媛2020;黄宗智2021)
李展硕博士的论文则使用“合作社”的用词来表达与杨团教授的“村集体”基本一致的实例和设想,其中关键在以农村基层社区为主体来综合社区的生产和销售等方面的活动。李所倡导的是来自革命时期历史中的基层党组织与合作社紧密结合经验的模式。与杨团教授倡议的今天的集体+嵌入基层的党支部设想,虽然在表达和名词、经验先例的依据等方面似乎不同,但实质上是来自相同的设想和实际——即既非资本主义模式,也非官僚主义行政模式,而是基于村庄社区的“集体”或“合作社”+基层党组织的党民合一进路。
张谦教授的文章纳入了众多他多年研究所积累的关于今天的小农场的不同细节,不少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张文关注最多的是今天占比较高的、我们称作“新农业”的一些重要特点,也是本著作集讨论最多的议题。虽然,张文并没有太多考虑到其自身在产、加、销“纵向一体化”层面所面对的挑战。那是我们其他几篇文章比较关注的问题。
在这方面,杨、李(也包括笔者)基本同意,当前的“专业合作社”大多乃是虚伪的合作社,实际上多是资本主义型的单位,与真正意义的社区 “集体”不搭界。我们认为,国家之前在这方面的政策主要偏向规模经济效益的教条,并不符合小农户、农村与农业实际需要的社区集体主导型合作社。但是,2018年以来,国家已经展示了前所未见的对小农户和小社区应对大市场的关注和扶持。这是一个新近呈现的重要动向。
本文载Rural China 21.1(2024)。
转载自:实践历史与社科研究公众号

